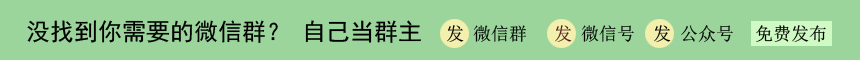毛娃没娘,说来话长。吃了冷亏的狼儿子,通过思前想后觉得是花姐和梁子合谋给他下了个套。狼儿子气的咬牙切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老子还是队长,早晚得让你梁子“吃不了兜着走,不信狼是个麻的”!但眼下重要的是先治病。
男人得了凉病在麻狼湾这个偏僻农村,就是在全世界,也是难言之瘾,羞于启齿,甚至讳疾忌医。狼儿子偷偷摸摸的在县城找了个老中医,号了脉,抓了药,连药渣都吃了啥作用没有。老婆问来的药方子也是“宋江的军师――无(吴)用”。
花姐和梁子开弓没有回头箭。如同从乏驴坡上下来的负重架子车,想刹也刹不住了。
花姐不顾爹妈“再跟人还得要彩礼”的话,直接就和梁子光明正大的住在一起。
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爹妈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再说,有个男人也好,省得寡妇门前是非多。
倒是便宜了梁子这狗怂,天上掉个肉馅饼,得了房院占了人。
开春了,队里的羊羔子,牛娃子,驴驹子,凡是公的都到了骟的季节。
骟匠把前绑个红布布的破自行车,又停到狼儿子院里。骟匠给狼儿子送来上好的漠合烟,银川白酒。
骟匠的巴结是因为狼儿子是队长,可以给他骟活。见狼儿子精气神不对劲,再看狼儿子女人瓦着个脸,皮糙肉厚,明显内分泌失调。几杯酒下肚,骟匠明白了这家的隐事。
骟匠说,吃啥补啥,把骟下的东西瓦罐白水熬,熬成汤汤,天天喝。熬过了的,切成片蓝瓦焙干,研成面面,天天吃。
狼儿子照做。没盐缺调料,怂腥气的难喝。但为了治病,毒药也得喝,
骟匠够义气,把其它队里的东西也拿来,供狼儿子不断货。
和花姐共枕的梁子,让队上的男人羡慕嫉妒恨:“夜黑了作梦真舒坦,梁子采了朵俊牡丹”。
谁的难心谁知道,梁子诉苦给发小:“肚子顿顿吃不饱,花姐天天缠着要”。原来,花姐瘾大火旺,不知细水流长,把个梁子缠的头昏耳鸣腿抽筋,精神恍惚忒累人。
梁子战斗力日落西山,苦不堪言。
骟匠又给狼儿子打听了一个治病的方子,病从凉上起,还得热中治。尤其三伏天的毒热头(太阳)。
狼儿子谎说上面有文件,加班加点干。让社员们正响午锄地,就是不休息。即使晒的蜕了皮,也把革命干到底。
梁子本就萎靡不振,甚至看见天上“几个太阳”。就大胆建议:伏里晌午热头毒,下午凉了咱再锄?狼儿子一听个“凉”字,火冒三丈,抢起胳膊就要扇,可巴掌还没挨上,梁子已经晕倒了。
花姐给梁子生了个儿子叫黑蛋。但就是这个儿子,让梁子心里堵了一块咧脚石,因为梁子知道狼儿子在这中间也插了一杠子。黑蛋的亲爹是谁?仿佛一个难题,凭梁子的本事是解不出标准答案的。或许是心理因素,看花姐怀里的黑蛋,咋看咋是个狼儿子。
补品快要断供。狼儿子竟把几个公羊,公牛,公驴也编个理由骟了。因为骟匠说,这些正在下苦的蛋作用大,一个顶几十个。骟匠还说,要是有一驴鞭,哪可不得了。
说啥来啥,没有麻搭。队里的一头公驴拴在电线杆子上晒太阳被绳子浪住,折了腿。狼儿子让人宰了,肉分着吃了。驴鞭在农村哪是没人要的,狼儿子说他拿去让黑狗吃。人们挣着笑,“队长比社员的狗大,吃去吃去”!
梁子是个勤快男人。冬天天还没亮就离开热被窝,早起拾狗粪。一是因为开春时,川区种水稻的生产队会来收狗粪,梁子就能卖些钱。二是梁子要躲过花姐早上的晨奋。
自哪次锄禾日当午晕倒后,梁子成了霜打的茄子。花姐也和他背靠了背,梁子就搬回了自己的家。想起过往梁子的眼泪花花把心淹了,心中的愁肠编成了苦曲花儿:吃不好,穿不上,夜晚睡的是冰炕。长夜难眠瞅月亮,我看黑蛋象队长。石头在心顶地慌!梁子上了花姐的当……
梁子身心疲惫,脑子受到刺激。有人见梁子背着背斗拿着拾狗粪的叉叉出了庄子再沒回來。花姐却在庄里女人的闲言碎语里,背上了“狐狸精”、“扫帚星”的骂名。
狼儿子得的凉病,老婆却害了心病。一条醋泡的骚棉裤,成了老婆心中永远的痛。狼儿子守口如瓶,老婆子百思不明。加上狼儿子又不顶个男人用,老婆既有心病,又得不到滋润,像秧苗久旱不见雨,天地在枯萎……狼儿子老婆怨恨自己命比王宝钏还苦。逐渐人比黄花瘦,终与世长辞走!
老婆走后,狼儿子感到内疚与空虚。公社通知开会,是传达包产到户政策的会。会后几个队长,担心包产到户单干了,自己的权力没了,心情郁闷,便打平伙喝酒,狼儿子更是不甚其烦,喝的大醉。
狼儿子走夜道回家岔了路,跌进一个洞里。和一个毛绒绒的动物一起,狼儿子以为狼,但实在醉的无能为力,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却是一个羝羊,跌进洞里时间长了没吃没喝,奄奄一息。
洞深狼儿子也上不去。宰了羝羊,用洞里的干柴,烧羊肉吃。过了两天,山上的羊把式发现了洞里冒出的烟,就把狼儿子救了。
狼儿子醉酒吃羝羊,眼睛重新泛绿光。又蹲在队部的塌墙上,见花姐正在热头下面,撩起衣服给黑蛋喂奶。哪露出的大奶奶,好像两面反射镜,耀的狼儿子眼睛绿了,喉咙干了,心呯呯了。不由自主想起与花姐的哪一夜,腰杆子突然硬了。
在哪里跌倒,从哪里起来……难道这都是命?狼儿子激动万分,一个冷奔子奔向自己家里,房门一开,屋里空空荡荡,老婆照片在墙……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狼儿子的队长也被村民选掉了。队里的地分了,粮分了,农具分了,羊驴牛也抓了阄了。圈里仅有的两头磨地牛,狼儿子抓了一头母牛,花姐抓了一头公牛。
春暖花开,干劲澎湃。两家的牛搭套变工开始了耕种……
——和一样,沐浴在春潮中麻狼湾村,一幅包产到户、万象更新的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作者简介:李向荣,男,六零后,现供职固原市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