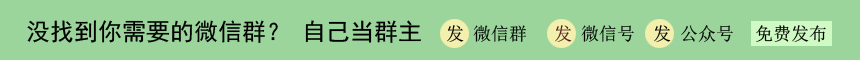儒家何以无“恶”与“根本恶”
——中西比较伦理的“消极情性”视角
刘悦笛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第116-123页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儒家为何无有“恶”与“根本恶”?以中西比较伦理的“消极情性”为视角,对于中西方论“恶”进行哲学比较,将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恶”的出场,证明西方思想有将恶加以“本体化”的倾向,而中国从来没有如此的思想取向。荀子所论之恶,并不是与善绝然相对之恶,善恶几成对称之关联的“二元论”在早期中国思想中并不存在,由奥古斯丁的“恶乃善之匮乏”之观念也不能来返观荀子。荀子从“消极情感”出发,认定情为先欲所困,后又下拉了性,由此以“欲-情”之恶推导出“性恶”,但“心善”却“化”性而勉于善。按照康德的“根本恶”观念,善恶的依据并不来自“意志”,而在于“意力”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却只能向善。比照而言,孔子的“我欲仁”之欲更接近于“意力”,孟子的“可欲之谓善”之欲则更切近于“意志”。就思维方式而言,西方探究“恶”之本源与中国的“向善”而生,分别来自于西方“两个世界”观与中国“一个世界”观。由中国看西方伦理的缺憾为:,西方持善恶对立的“二元论”;第二,西方的恶被本体论化了,成为人性之根。中国思想向阳而西方思想背阴,却把握到了全球人性的一体两面:善的谱系较之恶更为丰富,善有深度而恶则没有,尽管恶自有其广度。

中西方论“恶”之差异,中国偏“善”与西方重“恶”,曾几成共识,因之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比较观。但细思起来,中西之前参差抵牾之处甚多,需要进阶反思之。
“恶”:西方“恶”之本体化
在西方,“根本恶”(radical evil)或“恶”(absolute evil)的观念普遍存在。在中国,随“道性善”在宋儒那里成为主流,荀子的“性恶”论更被历史性地压制,到了程颐论定“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体已失”之后,恶似乎就成为中国的思想空场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从西方看中国,汉学家的判断极为准确:“与西方相反,将要被注意到的正是在中国,恶的概念不被察觉到,并不用总结性的词语来处理。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普遍的 ‘恶’与 ‘根本恶’ 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古老的中国传统中,更确切地说,恶被看做一种无能、一种偏心、一种背离自然原则、一种违背规范、一种对抗。有时它也可以被想象成为一种 ‘自然之恶’(natural evil)。但它既不是表示作为与善相对立的一种普遍的力量或一种的存在,也不是表示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推动前进的功能。”
这恰说明了中西方对待恶的方式迥异,西方主流思想善恶相对,恶是善的对立面,善恶被置于“二元论”的两端,善恶几成对称性关联。作为比照,老子所谓“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善的存在乃是由于存在不善(而非“恶”),善与不善也形成了彼此相生的有、无关联。善恶在中国思想那里不仅是互补的,而且形成了一种辩证互动。更为不同的是,西方不仅以恶对善,还把恶视为一种普遍力量,认定善恶二元对立推动事物发展,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当这种恶被视为“的存在”之时,就会孳生出“恶”之类的观念。
由神学出发的意义上,“的恶”与 “创造性的善”(creative good)往往相对而出。恶之所以被化,乃是由于恶是作为一种对善的“阻碍性的恶”(obstructive evil)而存在的。这种恶在三重意义上得以确立:种意义为恶乃是“无所不在”的,在任何情境下都是如此;第二种意义为恶乃“丧失资格的恶”(unqualified evil),反过来,对创造善有所建构则就不丧其资格了;第三种意义是就“恶是”(ultimate)的意义而言的,恶由此才成为的。这就意味着,其一,恶“”地到处存在;其二,恶由于丧失了善而“”地存在;其三,恶从而走向状态得以“”化,这就是“恶”何以的基本理由所在。
这便意味着,除了善恶二元对立,“恶”的出场,证明西方思想有将恶加以“本体化”的倾向。中国从来没有如此的思想取向,包括荀子在内,“为了恶的缘故,荀子甚至没有机会去想象或推理一种本体论的恶,一种对恶的吸引力,就其本身而论对恶的一种克制和奉献的存在”。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也绝不是如后世所见那么非善即恶或非恶即善,就好似A与非A是截然不同一般。清人钱大昕曾明言:“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荀子笺释·跋》)孟子是“尽”性而“乐”善,荀子则是“化”性而“勉”善,不仅原初二者就不相背,也恰是互补而相生的,这就是中国大智慧所在。

荀子言恶:从“欲—情”之恶推出“性恶”而“心善”
中国思想家论恶,首推荀子,千古一人。荀子如此定位“性—情—欲”的逻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以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荀子·正名》)然而,性恶的起源,却并不是自上而下地来自天,而是自下而上地发自欲。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根据“欲—情—性”的顺序,来勘定荀子“性恶论”的起源和根源。
唐人杨倞注《荀子》距今刚好1200年,根据其注:“性者,成于天之自然。情者,天之质体。欲又情之所应。所以人必不免于有欲也。”其实,从经验论的角度看,每个人皆有其欲,亦有其情,欲乃情之“感应”,抑或为情“应物”而动者。这里的问题就是,欲在情先,还是情在欲先?这个问题甚是复杂,有些欲引导了情,低级欲望大抵如此(这是“欲—情”);更有些欲以情为根基,大都是高级情感使然(此乃“情—欲”)。按照西方情感哲学的认定,情一定是有所指向的,倾向于有明确或具体的对象,一般并没有无指向之情,而欲则可以是无所指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建基在情感之上的。譬如,作为 ‘原始’的欲望如饿、渴,它们都是先于所有的情感和心情的,在匮乏的情况下,这些欲望作为极度渴望的反应激发出适度的情感。”
那么,荀子所谓的“欲”,究竟是哪种欲呢?《荀子·性恶》篇出现了几次论述,“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 ,这是生理性的欲望,耳目对声色;“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匮乏性的体验,于是,欲定在情先。还有在基本生理欲望满足之后,要夺他人之利的欲望,“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荀子·性恶》),在这种更为高级的欲望当中,欲也是居于情之先的。所以,在荀子所论的欲当中,欲是居于情先的,因为荀子所论之欲,大都是那种饱、暖、声、色、夺、取之基本欲望。由此,荀子才推出这样的结论:“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善者伪也”这个“伪”,一直以来被阐释为“做伪”之伪。但是,自从庞朴认定“‘伪’字原作上为下心,它表示一种心态,为的心态或心态的为,即不是行为而是心为”之后,对于荀子就有了新解。梁涛就接受了这种文字阐释,并认为这个“”字不是指“化性起伪”的虚伪,而是“指心经过思虑后做出的选择、行为,这不仅于文字有据,也符合荀子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的定义。故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理解为:人的性是恶的,善则来自心的思虑及行为”。由此,继续推出一种“性恶、心善说”,当然,徐复观更早就认定,荀子实际上是主张“性恶而心善”的。
然而,从伪这个字乃为“上为下心”出发,由此“化性而起伪”这个“伪”,就被阐释为心之伪,化“心”进而转为化“性”,这就把荀子给“心学化”了,这恐怕很难符合荀子的本意。这也就是说,荀子也被孟学化了,照此而论,孟荀统合以“心”为基调统合起来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孟荀各开孔子的两面性却被抹杀了。况且,这种“性恶、心善说”主张:在心的层面为善,为性的层面为恶,本善的心为上层,落到性的下层则产生了恶,这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混合人性论,更是后代对荀子的附加阐发之结果。
荀子性恶论的结论,大可不必从心那个高层向下推,而是要从欲的底层往上推:“失于欲”—“悖于情”—“反于性”,当然反性也就是走向了性恶论了。一方面来看“欲—情”之关联,“人之情,欲而已”(《荀子·正名》),“人之情,食欲有当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如此纵欲于色、声、味、臭、佚,就会走向“养其欲”而“纵其情”的偏失。另一方面来看“情—性”之关系,“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如此为之,就会成为“纵性情”而“违礼义”之小人。这也就是荀子的推理思路,也就是由“情恶”推出了“性恶”。
照此而论,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他们看待性之善恶,恰恰是受到了他们对待情之立场和态度的左右。相比而言,孟子只把情视为“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feeling)的话,从“恻隐之情”的四端之始到是非之心的四端之末,孟子所见的人类道德的基本情感都是积极的,也都是善的。荀子所见之情则皆为典型的“消极情感”(negative emotion/feeling)。在荀子的“欲—情—性”的逻辑架构之内,情为先欲所困,后又下拉了性,由此导向了性恶论的逻辑终点。
再往上看,按照荀子的观点,性来自天,性是自然属性,但问题是,荀子究竟是从先天还是后天言性恶的呢?如果说,人先天就是恶的,那么性本恶,这就有点接近西方人性恶的思路了;如果人后天变得恶,那么则是说,以情应物时,不节欲而倒向了恶,而且是“情恶”推出了“性恶”。更准确的说,乃是“欲—情”之恶,而非“情—欲”之恶,导致了性之恶。如此看来,荀子更多是从后天论性恶的。但必须指明,在原始儒家那里,“性”绝不是本质化的本性之“性”,而是一种逐渐的生成过程,从而不同于那种固定而现成的“人性”存在。
荀子本人其实照顾到了先天与后天的两面性,性自天生,这是先天的,毫无疑问,“生于人之性情者,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感而不能然,必待事而然后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然而,性之所以为恶,更多是后天形成的结果。历史学家吕思勉评价得很准确:“荀子谓 ‘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 ‘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则孟子亦未尝谓此等修为之功,可以不事也。”这就是说,说人性“不能生而自善”,也并不是说性本即恶,孟荀的目的皆为向善,荀子更为注重后天修为,孟子则更为注重发见先天,说孟荀有如此之别大抵没错。

荀子
“恶乃善之匮乏”:从奥古斯丁无法返观荀子
中西比照的关键,还在于荀子本人如何看待“恶”?《荀子》的《性恶》篇一般认为是荀子后学所作,并不是荀子本人的亲笔,这里也存在着微妙的思想差异。《性恶》篇直接针对孟子性善论,并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否定,先引述孟子曰“人之性善”,然后“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按照当今的理解与阐释,既然孟子道“性善”,荀子主“善恶之分”,直接否定性善,那么,荀子也有了善恶决然相对的观念,孟荀之间在人性论上绝无调和的可能性。理由就在于,性恶之“恶”,被理解为善恶决然对立之恶,然而,这种对恶的理解就化了。但仔细揣摩,荀子所言之恶,似乎仅是“不善”的某种程度之相对概念,绝不是西方那种“恶”抑或“基本恶”的概念,这从中西恶论比较当中就可明显得见。
“恶”其实乃是某种程度的“不”善或“非”善,正如孟子所说的“不善”乃是不足之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荀子的性恶来自“性不善”的讹传,“性善的反命题是性不善,先秦论性以善、不善对说,汉以来流行善、恶对说并各配性情、阴阳等”,这种历史梳理笔者基本赞同。由此可见,“‘恶’不是与善对立的概念,恶因此被解释成不能发展自身的潜能,不能与道协调。孟子之恶不是恶的一个积极概念,而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概念。他把恶想象成从存在中减少。而不是添加的某种东西:它是一种丧失,是一种某种不可能存在,而又应该存在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善在孟子那里是一种加法意义上的“积极概念”,恶在荀子那里则是一种减法意义上的“消极概念”,做加法的孟子不断在善上做增量而压倒不善,做减法的荀子在恶上做减量而避免不善,孟荀恰恰殊途同归。
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统合孟荀和道统重估”学术研讨会上,当笔者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有论者提出这不过就是奥古斯丁的“恶乃善之匮乏”的观点,现在要就此做出反驳。荀子言恶,很容易令人联想起这位“教父哲学”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奥古斯丁似不太讲恶,认为恶只有缺乏义,恶就是善的亏缺而已!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其核心著作《论信望爱手册》的第十章表述为:“至善的造物主所造万物皆性善” ,“万物都是至善、同善而恒善的三一真神上帝所造”;第十一章则表述为:“宇宙中所谓的恶,只是善之亏缺而已。”分而述之,善之缺乏,如动物伤病就是健康之缺乏,伤病之“恶”就是健康之“善”的缺欠,而且属于偶然而非必然的,“灵魂的罪”也只是人原本之善的缺失。
按照这种早期神学观,上帝无恶,因他的善是完全的善,“含恶之善”是有缺陷或不完美的善。有缺陷的善是带有恶的存在,就存在本身而言,它仍是善的,于是,善的才是恶的。因而,只有善才能成就恶,“完全没有善的地方便不会有人们所谓的恶。完全没有恶的善是完美的善。含有恶的善是有缺陷或不完美的善,没有善的地方恶也将无存”。这种观点看似辩证,但是却预设了“犹太-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上帝被认为是无限的、人格性的永恒存在,它创造了所有除它以外的所有存在物,上帝在其被造物的前面展示了圣的、爱的完美自身,后有“神正论”为证。
然而,这种神学观念,在荀子那里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神学割裂出现世与来世的“两个世界”,而在荀子那里只存在现实的“一个世界”。于是,中国早期思想家,无论是孟荀还是老庄,,皆缺失“一神论”的观念;第二,认定善没有(为“恶”的)真正的对立面;第三,物质与精神也是统合为一的;第四,终认定“恶”具有相对性,而不可能让恶走向。所以说,荀子所说的恶抑或不善,并不同于神学意义上的“善之匮乏”。中国原始儒道思想更为杂糅地来看待善与恶,道与器之间也是不即不离的关联,不仅未将善恶撅分两截,且更不可能走向善恶观。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真正伟大之处,乃是看到了“自由意志”在道德当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正反两面,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奥古斯丁区分出三类恶,一类是物理之恶(如生老病死自然灾难),一类是认知之恶(人类理智不完善),还有一类就是伦理之恶,这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缺憾所在。据奥古斯丁《论信望爱手册》第三十章的观点:“人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善行⋯⋯因为人类正是因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毁坏了他的自由意志并他自己。”这就是说,人借用自由意志而行恶的话,那就败坏了自由意志和人类自身,“人在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犯罪时,其意志的自由便丧失了,成为罪的奴仆,只有犯罪的自由。他们在离罪之前没有行义的自由”。
这种自由意志论,大概与实用化的荀子相去甚远,而与理想化的孟子极为接近,因为孟子始终高扬一种“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之道德自由意志力量。但孟子却只见道德之善的正面威力,却未见自由也带了恶的负面。的确,恶在道德上之所以产生,恰与人类的自由相关:“道德上的恶的可能性,是和人的自由相随而生的,现在如果我们从道德上的恶的可能性转向考虑实际上的道德性的恶,我们会发现,虽然道德上的恶有可能发生,但对它却无法加以解释。因为对于一件自由的行动,我们没有办法作完整的因果性的解释;假若我们能在因果性上加以解释,这行动便不是自由的行动。道德上恶的起源,永远隐藏在人类自由的奥秘当中。”这就道明了,恶也是源发自人类自由的,其中还包含着悖论之处。
康德论“根本恶”:“意力”无所谓善恶,“意志”则只能向善
“根本恶”这个拗口的中文词,一看就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还曾被翻译成“激进之恶”“基本的恶”诸如此类。提到“根本恶”的观念,做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时间就会想到康德,康德的确是较早给了根本恶以规范性规定的哲学家之一。实际上,根本恶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基督教传统内部,但在康德那里,人根本为恶的,却得到了哲学高度的理性化论证。按照如今的一般研究,康德之“恶”的概念,如果被简约到根本处的话,主要依赖于三个假设:“,恶构成了人类意愿的根基性的意向(因此恶才成为 ‘根本的’);第二,恶构成了自爱原则(the priciple of self-love)的首要动机;第三,恶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普遍习性。”这就意味着,恶由于其根基性、(对自爱原则)首要性和普遍性,所以才能成为“根本恶”,其中条为基础,但是这些假定都有所争议,那么,恶到底是不是人类的原初性的普遍习性呢?

康德
实际上,康德明确反对从人的“自然倾向”里面去寻恶的根源。“人的本性的恶劣,不能那么准确地被称为恶意。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它是指一种把恶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故而这准则是魔鬼般的)的信念(准则的主观原则)。相反,它应被称为心灵的颠倒,这个心灵就其后果而言又叫做恶的心灵。这种恶的心灵,能够与一个总的来说善的意志共存。它产生自人的本性的脆弱,即在遵循自己认定的原则时不够坚定,而且与不纯正性相结合,没有按照道德的准绳把各种动机相互区分开来。”按照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当中的观点,善是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恶也是发源于人的自由的。通常而论,人们都愿意把恶的根源,归咎于人的自然倾向,譬如孩子搭起积木后都推倒那种破坏欲,就是此种倾向的某种原初显现。然而,康德显然否定了这种自然人性论的主张,在康德的阐释者反而认定,其一,“自然不会产生恶,只有自由的人类意志才会产生恶”; 其二,康德“甚至都没有说自然倾向的存在是中立的(既非善又非恶的),而是说自然倾向实际上是善的” !
按照上面种阐释者的观点,说的是“自由的”人类意志带来了恶,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对了“自由意志”,却说错了“意志”,意志在康德那里也不能产生恶。“自由意志”作为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其中所具有的那种强理性主义,其实也是一种理性强权,由此也就抹杀了情感与感性在伦理和道德当中的本有功用与平衡。当人类意志被自由使用的时候,恶就由此可能产生,但是在提升为自由意志之后,那无疑只能向善了。更为关键的区分还在德文意义上的“意志”(Wille)与“意力”(Willkür),这在康德后来那里是有明确区分的,即使在英文中二者都被简化译为“Will”。康德本人也是如此,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模糊地使用了这两个词,笼统地从“意力”视角来论实践自由,但是到了《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和《道德形而上学》当中就明确区分开了二者,这对于理解恶与根本恶而言至关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按照康德的看法,善恶的依据并不来自“意志”,而在于“意力”的自由选择。这个Willkür,在德文中本有“随心所欲”的任意、任性之意,其实翻译成“意能”似也准确,也就是“意(欲)能(力)”的意思。按照哲学家伯恩斯坦的阐发,“意力”作为在可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善恶当然是主要的可选项),“从本质上说,它既非善亦非恶;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自由选择善恶准则的能力⋯⋯意志指的是意愿能力中纯粹理性的方面”。按照康德研究专家艾里森的划分,“意力”具有“执行功能”,而“意志”则具有“立法功能”,对人类意愿能力的这个归纳实在太准确了,因为执行者不必一定明善恶,但立法者则必定向善避恶,“意力”可能走向恶,但“意志”一定导向善。
道理在康德那里无比简明,作为自由法则的“意志”命令,一定且只能走向道德自律。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意志”,可不是那普通的日常意志,而是属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高级“意志”。如果说,“意力”或“意能”作为一般的实践理性的意愿,还有善恶可做选择,既可遵循也可违反道德法则,但对于纯粹理性的“意志”而言,根本没有善恶的选择可能,“意志”只是且永远是善的,否则它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本价值。
由此再来反观孔、孟、荀论“欲”,康德的语词分殊对于更明晰地理解和阐释儒家也有。孔子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个欲仁之“仁”,毫无疑问乃是“善”之仁,具有仁之“善”的特质。尽管如此,欲仁之“欲”,却更接近康德的“意力”,因为孔子本人始终未明言性之善恶,更倾向于持中性立场。孟子就不同了,当他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这个可欲之“欲”,就更为切近康德的“意志”。由于孟子自有“情善”“性善”“心善”论的强大道德标杆力量,所以他才会强调那个“求则得之”的“在我者”(《孟子·尽心上》)。既然“在我”,那就无疑凸显出道德主体意志的自由力量了,相形之下,荀子则强调“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性恶》),那种欲则就是导向非善趋“恶”之欲望了,从而不同于孔孟之“欲”那种道德意愿了。
按照上面第二种阐释者的观点,伯恩斯坦说康德并不持有自然倾向上的中立论,而更倾向于认定人的自然倾向实为善,这其实乃是相当接近孟子“性善论”的一种阐释,但却根本殊途。康德的确明确说人原初的“自然禀赋”(predisposition)乃是善的,说人是被创造为善,并不是人已是善的了,善恶取决于人的“意力”选择,而是说,人被创造为“向善”(for good)的。

孟子
孟子也持类似的观点,孟子似乎并没有说,作为生成性的“性”,就本质而言乃“是善”的,而是说诸如恻隐之心这样的“善端”之端,就是“向善”而生的。康德也有近似的论述:“在我们身上重建向善的自然禀赋,并不是获得一种丧失了的向善的动机;因为这种存在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机,我们永远也不会丧失,要是丧失的话,我们也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它了。因此,这种重建,仅仅是建立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所有准则的根据的纯粹性。按照这种纯粹性,道德法则不是仅仅与其他动机结合在一起,或者甚至把这些动机(性好)当做条件来服从,而是应该以其前全然的纯粹性,作为规定人性的自身充足的动机,而被纳入准则。原初的善也就是要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方面准则的圣洁性,因而是单纯出自义务的。”
由此可见,在寻求“原初的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上,孟子与康德并无分歧,但是在如何寻求“原初的善”之道德根据之时,那就大相径庭了。因为,康德使用的是一种“上求法”,力求寻求道德法则建立的根据。由这种纯粹性的探求出发,道德动机也就被纳入道德准则之内,甚至“原初的善”也成为了一种道德义务。成为道德义务,那就诉诸于理性而不参杂任何感性成分。然而,孟子所论的原初的善,譬如看到孺子将入井所生的恻隐之心或惕悚之情,则是情理合一的结构,而且其中尽管情占据了主导,理性亦暗伏其中。由此反过来再观康德,从原初的善到道德义务,这一步究竟是如何跨越过去的,那就值得质疑与怀疑了;而孟子则是以从(情大于理)恻隐之心到(理大于情)是非之心的自然过渡,来实现这种无缝衔接的,那么中西伦理逻辑,到底哪个更符合人类情性之“道”呢?
探“恶”本源与“向善”而生:西方“两个世界”与中国“一个世界”观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的大问题:中国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体系里,为何没有“基本恶”与“根本恶”的存在?这是个共时性的问法,也是中西比较式的问法,还可以换个历时性的内部问法:为何越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中晚期,性善论越位居主导,而性恶论却丧失了其历史地位呢?当然,历史学者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给出各种答案,毕竟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但是,中国没有“基本恶”与“根本恶”,更为倾向于认定“性本善”,这个问题还是有其哲学解答的,这关系到中西方思维的根本差异——西方“两个世界”观与中国“一个世界”观。
这种中西差异,较早来自安乐哲的论述,李泽厚对此反思更深。安乐哲在《孙子兵法》英译导言里面,提出西方“两个世界理论”(two world theory) 与中国“这个世界(此世)视角” (this world view)之分殊。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占领了古希腊思想,其所统领的就是“两个世界理论”,后来随着从古希腊哲学到犹太-基督教哲学的发展,二元论的思维模式(“d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便成为了范式,一直影响至今。所谓两个世界,就是指古希腊哲学家与基督教父们发现了实在的世界与变易的世界之分,并将二者区分开来形成了世界的分裂。由古希腊与先秦中国比较来看,中西思维方式也被区分了开来。
中国思想由于秉承了“一个世界”的观念,并没有形成古希腊哲学那种作为原则的“形而上学”观,也就不去追问“多”背后那个“一”到底是什么?普遍到底由何而来,且谁造成了这种普遍性?
郝大卫的解析其实更为深入,他认定中西方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亦即“与第二问题式思维”(first-and-second-problematic thinking)。问题式思维:使用了说明现象世界中个别(具体事物)的解释;第二问题式思维:对实体和本体的特征给予了理性的或逻辑的解释。这两个问题式差异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思维重“生成”(becoming)与西方思维重“存在”(being)之分殊。这意味着,中国重原始的直觉或更普遍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是现象学的过程、变化和变成的经验,西方的思想则与作为不变的基础的“存在”紧密相联,由此善于追问本体论的根源问题。
如此看来,既然西方思想源于本体论,而中国哲学青睐于现象学,那么,这就为“恶”与“根本恶”的提出提供了思想的根基。恰恰由于,西方人青睐于给恶寻求一个“本体论上的基础”,所以才创造出“恶”与“根本恶”诸如此类的命题。这是源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迥异:“西方思想起源于本体论的问题,而中国哲学则首先是现象学的,因其承认经验世界的存在不必借助于假定的本体论依据。现象学的世界是通过相关性的运作而组织的,而相关性的运作之间是通过类比性的分类而不是求助于本质、范畴或自然类而联系起来的。”荀子论恶就是如此,他没有给予恶一种本体论根据,而是在“欲”之恶、“情”之恶、“性”之恶与“心”之善等一系列相关思想之间做出了关联性探究。中国人从古至今从未将恶加以根本化或化,历史渊源与逻辑缘由大概就在这里。
从中西“恶”思维的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哲学思想对于“消极情性”有着不同的解答。性恶论就是一种“消极人性论”,情恶论则是一种“消极情感论”,“恶”与“根本恶”思想则将消极情感与消极人性论推向了状态。这恰恰由于,西方崇尚“两个世界”的分离,恶的根源并不仅到现世当中去寻,而是要到“另一个世界”当中去探求“恶的本源”。中国自孟子开始,上经思孟学派的“自然人性论”,直到宋儒的“先验人性论”,大都需求“善的根源”。只不过,中国后来更倾向于从一种“消极情感论”和“积极人性论”的角度来探求,情恶而性善,欲恶而心善,由此性善论也就成为了古代中国中晚期思想的主流线索。
从全球人性论的角度看,善与恶,并非一个圆环光谱当中相对的对称两面,并非如西方人所见乃是善恶二元的对立。善的谱系更具有丰富度与深入性,恶反倒没有那么多的维度。当然恶的破坏力较之善的建构性总是更显巨大。善有深度,而恶却没有,尽管恶自有其广度。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意义上的极恶之人并不存在,他也有善,哪怕是就有一点点善念在。但圣人却真实存在,无论是在宗教还是世俗社会里都存在,这就是善与恶的不对称性。大概在中西善恶论上,中国人更愿意面对阳光,而未见阴影一样;西方人则更愿背向阳光,而面对阴影一面。这也许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大致取向不同使然。
尽管善恶不可分离须臾,但从中国看西方的缺憾确是显见的:,西方持善恶对立的“二元论”;第二,西方的恶被“本体论”化了,成为人性之根。“根本恶”与“恶”,恰恰源自西方“两个世界”之分,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恶之本,所以才有此论。中国“一个世界”观,就没有此种取向与割裂,善恶只有在这个世界在,而恶却不可能被与本根化。在西方,被先在给定的上帝可谓至善而无恶,恶不能作为宇宙构造的基本部分而存在,但中国的圣人的养成则是个“生成”的完善、完美、完满之过程,而不若现成的一神教人格神的那种道德完美无缺。
性善论乃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发展成熟的产物,这来自徐复观的历史观点,因为性善论“是继承文化上长期道德反省所得出的结论,没有选择的自由,便无所谓道德;所以他只把在生而即有中,人可以自作主宰的一部分称为性”,所以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到孟子而始发展完成。 孟子性善由心善而出,“从人格神的天命,到法则性的天命;由法则性的天命向人身上凝集为人之性;由人之性而落实于人之心,由人心之善,以言性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经过长期曲折、发展,所得出的总结论”。当然,本文只是探索了中国为何无有“恶”与“根本恶”,尚未探求另一个一体两面的大问题,中国为何是“向善而生”的?这需另文详述,但笔者更倾向于从一种“积极情性”的独特视角来加以阐述。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