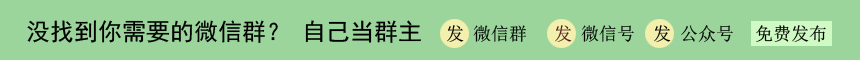我们行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天时就是根据天象选择恰当的时机。
近日,全世界的航天迷都获悉了一个好消息:继“天宫二号”在轨运行两年多的时间,即将受控离轨之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发布了,来自17个、23个实体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批科学实验项目。

众所周知,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内,中国空间站可能是的空间站。这标志着我们中国人将作为牵头人,带领多国人民共同开启一段太空探索之旅。对此,大批的太空迷或已翘首以盼了,而回首我国航天事业的漫漫路程,如今这番成就确是极其不易。
假如我们倒回到200年以前的清朝,甚至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里,私自架起一台设备观察天上的星星,可都是要杀头的大罪。
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从远古时期直至现代,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头顶这片天空的探索和思考。西方的天文学家很早便提出了地球是一个球体的设想,并且不断运用数学知识归纳观测数据,提出多种模型论证天体运动是完美的、和谐的圆周运动。他们把天体规律看作是纯粹无暇的体系,彰显着神明的圣洁,以至于把已观测到的太阳黑子、彗星、流星这些东西归结于地球的大气现象。他们绝不愿承认有多余星体,以免破坏了九大行星体系的神圣。

彗星(资料图)
而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是农业社会,自尧舜至清朝,农耕一直是万众国民的要务。围绕这一任务,古人基于对天空的观测总结、推算出了“二十四节气”和越来越精细的农历法,以有助于百姓从事农耕活动。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确立了阴阳合历的原则,制历需考虑“日、气、朔”三个基本要素,即太阳活动、二十四节气以及月球处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昼夜不可见的朔望月,三者之间在历法中要通过计算达到均衡。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尚未确立天体圆周运动的规律,但却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推算出了回归年和朔望月的规律,加以运用。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战国时期,我国便有了以365.25天为一年的“四分历”,十九年置七个闰月,以消除每年0.25天的误差。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张衡、祖冲之等天文学家更是将观测技术、仪器设备不断更新,天文成果也不断刷新。张衡的漏水转浑天仪由漏壶和浑天仪组成,浑天仪是一个刻有二十八星宿、黄赤道、南北极、二十四节气的铜球,在水流的推动下,模拟天空的运动,形象地展示了张衡所提出的“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是说大地就像蛋黄,天如同蛋壳包裹着地。此等把大地说成蛋黄的说法,显然未对普通百姓造成太深的影响,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古人们,如何想象眼前的万里平原是个球面?

浑天仪
祖冲之则借助自己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的成就(领先世界一千多年),推算出回归年长度为365.2428148日,与今日的推算值仅差46秒。他所编撰的《大明历》中,每391年设144个闰月,这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精度。
既然历法为农业服务,农业受气候、土壤性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天时历法真的有必要精确到小数点后这么多位吗?前文提到,古时的人们架起设备观测天象那可是死罪,为何张衡、祖冲之等精于算术的天文学家能做出此等成就?
一切都要从深深根植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说起。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姜太公制定周礼开始,我们这片土地上历经多次改朝换代逐渐形成了一条默认的法则:统治者是奉上天的指示统治万民的,自称“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儿子,老百姓自然拥护。但是如果天子本人荒淫无道把百姓往死路上逼,那么就会有其他的仁君奉天意前来讨伐。这也是我们常听的那句“奉天承运”的来由,皇帝下达的圣旨一开头就会表明自己奉上天的旨意管理的正统位置。

姜太公(影视剧照)
既然是天的儿子就必须时刻关注着天所传达的信息。在每个封建朝代,各种异常的天象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天文现象,天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应着地上相关的人或事,此可谓视作“天人合一”的表现。由此,不寻常的天象往往会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大臣会利用异常的天象劝谏皇帝,采纳对有利的建议,皇帝也会利用异常天象铲除异己。
在广受好评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中,个镜头便是一位钦天监的官员直言上谏嘉靖皇帝,陈述了朝廷政策混乱,官员贪污腐败致使天降不详——京城整个腊月都没降瑞雪。然而这位官员却因诽谤朝廷的治理能力,受廷杖惨死在宫门外,由此引入了严嵩一手遮天、朝廷内部明争暗夺的一系列故事。

嘉靖皇帝
钦天监就是明朝皇帝设立的专门观测天象的部门,除皇家的天文部门外,皇帝决不允许有观天的民间行为出现,盖因政治维稳的考虑,天子需垄断上天传来的各种信息。中国古代的皇家天文台从秦汉时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宋元两朝的司天监以及明清的钦天监,虽然几经易名,但天文台的观测从不间断,天文工作者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前文所提到的张衡、祖冲之便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希腊的天文学家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中国的天文学家和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在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供职,依照礼仪供养在皇宫高墙之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天文学”一章开篇即介绍了东西方天文学家的差异。而令人唏嘘的是,我们熟知的给天空“立法”的伟大天文学家、数学家开普勒就是被自己的金主拖欠了二十多年的工资,病倒在了讨薪的路上,结束了穷困潦倒的一生。

李约瑟
历史记载公元前178年有一次日全食,当时的汉文帝在日食期间素服斋戒祷告上天,并下《罪己诏》说:“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渺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异常天象除了能促进执政者反省自身以外,也会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故而古代的天文学实在是一门影响深远的学问。
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要务就是详尽,务必要把天上的所有信息详细地捕捉到并记录下来。来华传教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中对皇家天文观测者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生动的描述:“五位数学家每个晚上都守在塔楼上,观察经过头顶的一切。他们中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守望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样,世界上四个角落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辛勤观测。”相比之下,西方人感叹他们的早期学者常无视异常天象,也未对彗星、太阳黑子、新星、超新星有过记录,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记录上却独领风骚。

太阳黑子喷发时会释放数百万吨电离气体
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七年)到公元1910年(宣统二年),哈雷彗星共29次回归,共发生过925次日食、574次月食,100多次太阳黑子全都详细记录在案,在天文记载方面,中国毫无疑问居于世界首列。在此历代传承的基础上,科学史界的泰斗席泽宗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的研究,即其考订论文《古新星新表》,被认为是整个20世纪中国天文学有影响力的论文,被世界各地的天文学者广为引用。席泽宗也因此成为一位研究科学史的科学院院士。
中国古人有着傲人的天文观测成就,以致许多人提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领先于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后才落后”的说法。该说法认为古代中国自上而下始终把头顶的苍天看作一个有意识、能辩善恶的神明看待,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成就也大多被用作类似于西方占星术的研究,从观测到尝试解密其规律,我们一直在思考苍天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指引。我们行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而天时就是根据天象选择恰当的时机。历代的观星家解密天空密码、编制日益精准的历法以及记录各个黄道吉日的老皇历,百姓的婚嫁丧葬、动土上梁以及农耕社会的各种重要活动,都根据这份“天时解密手册”来判断何时为宜,何时犯忌。

哥白尼
如《易经》所载:“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大批西方的传教士运用他们发达的技术,多次展示西方科学在预报日月食方面更为准确的情况下,帝王们也只想到了录用西方人入职钦天监。直到皇权政治解体、新文化运动以后,国人才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头顶这片天空。
幸而我们奋勇直追,突破了种种技术封锁,靠着我们民族从古至今一直都在闪烁的智慧,即将会迎来天文探索的又一次高峰。
参考文献:
[1] 什么是科学/吴国盛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8
[2] 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4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8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